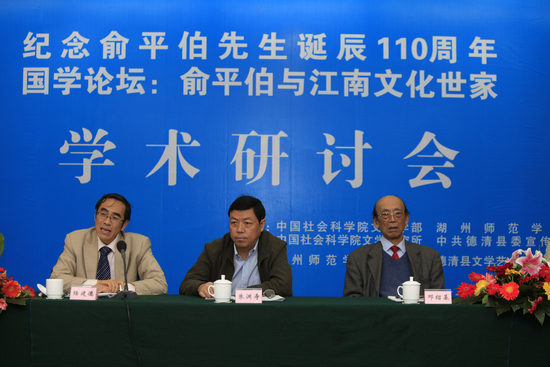投稿系统
投稿系统
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学术活动
俞平伯先生,名铭衡,字平伯,以字行。德清县东郊南埭村(今城关镇金星村)人。俞平伯先生学贯中西,在“五四”以来新旧诗词、小品散文、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均有建树,业绩非凡,卓为名家。
为了纪念
在蒋云良副院长代表湖州师范学院所做的的大会致辞中指出:联合举办“国学论坛:俞平伯与江南文化世家”学术研讨会,是一次有益的尝试。湖州是文化之邦,可以研究的文化世家还有很多,如赵孟頫家族、钱玄同家族、南浔董氏家族,沈氏家族更是从南北朝时的沈约延续到现代的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三兄弟。“国学论坛:俞平伯与江南文化世家”学术研讨会应该是个良好的开端。
来自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等单位的5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俞平伯与红学;俞平伯与中国新文学和德清俞氏家族与江南文化世家等主题做了专题学术报告。
一、俞平伯与红学:
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1922年顾颉刚在与俞平伯的通信中称胡适的红学为“新红学”。1923年俞平伯出版《红楼梦辨》。
余英时的《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把半个多世纪来红学研究的不同理路作了比较清晰的梳理,而且借鉴孔恩的典范理论,指出胡适可以说是红学史上一个新“典范”的建立者。得到学术界广泛认同。《红楼梦辨》1923年出版标志着新红学的重要实绩和标志性成果,俞平伯先生日后成为海内公认的新红学大师。对于新红学90年的来的学术发展,特别是俞平伯先生与新红学,成为与会专家一个热议的话题。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邓绍基研究员《缅怀
作为新红学的奠基人之一的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刘扬忠研究员《
说《红楼梦辨》在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上具有开创意义,这个评估丝毫不过头。俞平伯具有诗人和文学史家的双重身份,他充分了解和熟悉文学创作的规律。和旧时的评点派和猜谜派不同,他把古典小说当作文学作品看待,把古典小说研究当作学术对待。《红楼梦辨》这一空谷足音似的早期成果,使刚刚接受了新学洗礼的“五四”时代的读者们清楚地认识到:古典小说是古典文学中重要的分支,应享有与“正宗”文学同等的地位。从此,小说研究在学术工作中的地位日渐提高,后来者研究古典小说所取得的成绩越来越多。可以说,以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的《红楼梦辨》的相次问世为标志,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观念解放了,方法更新了,领域拓宽了,门类齐全了,向现代科学迈进的步子加大了。
过去论者常常将俞平伯的考证和胡适完全等同起来,不明白在俞平伯那里,文学和审美的趣味极为浓厚,将文学还原为文学来进行仔细研究的观念远比胡适明确和坚定。这就导致长期压低了俞平伯在古典文学研究史上的位置,是十分令人遗憾的。《红楼梦辨》比胡适《红楼梦考证》进步的最主要之点就在于:它严格地将一部古典小说作为文学来进行考证和评论,摆脱了文史不分的混沌模式,取得了文学范围内的研究实绩。
俞平伯的红学论著,在下列三个方面具有开创意义:
(一)把我国古代最伟大的一部长篇白话小说还原为文学现象来加以研究,抛弃了旧红学“索隐派”的猜谜式的反科学的方法,用材料考证与艺术辨析相结合的新方法,从作品本身出发,把作品同作者的身世、思想、生活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使《红楼梦》研究从此开始走上了科学的轨道,促进了对该书创作过程的了解和创作方法的研究。
(二)俞平伯作为一个融旧学与新学为一体的内行的文学鉴赏家,始终把《红楼梦》这部代表着我国古典文学最高成就的作品,放在审美鉴赏与批评的层面上,对它的艺术风格、美学内蕴,特别是它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系列,做了长时间的深入细致的探究,进行了许多切中肯綮的分析和阐述。这就超逾了胡适等人偏重于历史学层面的考证的狭小框框,开辟了对《红楼梦》进行美学观照的广阔道路;并为《红楼梦》鉴赏提供了具体的示范,打破了旧式小说“评点”派的一统天下。
(三)俞平伯又是《红楼梦》版本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对《红楼梦》原稿的考证和佚稿钩沉做了大量艰苦细致而卓有成效的工作。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孙玉明研究员在发言中说:在红学史上,浙江出现了许多红学大家,例如王国维、蔡元培、鲁迅、吴世昌等等。仅德清籍的就有三位重要人物:第一位是戚蓼生,我们所说是戚序本,就是因为卷首有戚蓼生的序。这篇序言,历来为研究者们所广泛引用。第二位便是
湖州师范学院刘方教授在《学术趣味与范式迁移:俞平伯《红楼梦辨》学术新质的再思考》的发言中认为:《红楼梦辨》1923年出版标志着新红学的重要实绩和标志性成果,
如何形成、产生这一差异?历来研究者不重视学者个体的文学趣味、个性气质等等,如何参与到学术研究中成为潜在影响因素。虽然因为时代大潮的影响,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极力迎合、认同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所提供的新范式,但是仍然不能够完全一致,在不经意间,潜移默化影响,在成为新红学的标志成果之一,为新典范作出贡献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也在调整、迁移这一范式,从而为范式迁移的产生,埋下了种子。
文学趣味、审美趣味与学术兴趣所在,俞平伯与胡适明显有差异,构成了典范转移的潜在支援意识与知识构成。俞平伯的文学趣味、文学欣赏传统文学的直观、体验、感悟、鉴赏、品味,俞平伯此后的学术研究也多是体现这一方面的成果,而其新诗特别是散文等方面的文学创作,同样体现如此,特别是对于传统文学的借鉴与吸收。胡适则历史癖与考据癖,缺乏文学欣赏的趣味甚至能力。而这种趣味的形成,既有个体气质、教养、家庭环境影响等等也有对于外部环境、学术评价的认同而强化、迁移。从两人一生的学术与文学创作来看,鲜明反映了两个人性格、气质与差异。俞平伯不仅新诗成就颇高,而且深得传统文学精髓,其研究文章,论诗论词也颇能深入文心。有良好的对于文学的感觉、领悟能力。而胡适除了一次不算成功的新诗尝试,之外,几乎都是史家本色的文史考证文章,鲜有能够鞭辟入里的文学文本分析。正是两个人的审美趣味,天分与学力,性格、气质的差异,导致前理解结构、前见的差异,形成《红楼梦》研究范式上的变迁与差异。
俞平伯《红楼梦辨》是趣味重构下的产物。同时,旧有的趣味又不可能完全脱胎换骨,形成某种基质、底色、前理解和支援意识。导致《红楼梦辨》对于胡适新红学范式的无意间构成的典范转移。虽然书中一部分内容涉及版本,也是比较分析不同版本的文字,仍然是文学研究。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学术研究的趣味,着眼点,受到其潜在审美趣味的影响与制约,形成新红学典范中与胡适典范的差异,从而构成了新红学的典范转移。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孙丽华副研究员《“左钗右黛”还是“钗黛合一”?——
像《红楼梦》这样一部巨著,内容纷繁浩瀚,然而由其中两个特出女性的比较对照,我们却可以找到理解作品的肯綮要义。在这个方面,
纵观延续到当今的红学发展,我们不禁慨叹俞平伯先生始于20世纪初的红学研究已经奠定了学科发展的大的方向。正是由于有俞平伯先生那样的基础厚重又覆盖全面的总体性研究高屋建瓴,导夫先路,虽然经历了各种曲折与干扰,但是当研究环境回归正常以后,健康的红学研究所体现出来的发展方向,仍然延续着将近一个世纪以前由俞平伯先生所开辟的社会历史—美学的道路,时至今日,在红学的领域里,已经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前辈学者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是我们不应该遗忘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夏薇博士《但开风气不为师——浅议
我们可以从红楼梦研究史上看关于《红楼梦》后40回作者的研究,并可以从中看到与时俱进的
二、俞平伯与中国新文学:
俞平伯先生是“五四”以来集“作家”与“学者”于一身的著名人物之一。作为一位作家,他的新诗与散文的创作卓有成就。与会专家在这个方面同样发表了新的研究、观点。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陆永品研究员《爱国诗人俞平伯在新诗歌史上的贡献》发言中认为:俞平伯在新诗创作实践上的贡献:一他是白话诗创作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1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积极参加白话诗创作,写了大量新诗。与胡适、郭沫若、朱自清等皆为著名的白话诗人;为新诗创作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为新诗创作做出卓越的贡献。2对反对新诗的遗老派,给予了尖锐的批评。无疑,俞平伯批评反对新诗人的观点是正确的。二他正确阐释了文学的性质,反映论和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从俞平伯关于文学的反映论来看,即说明文学就是人学,所谓“文学就是人学”的观点是极其错误。在新诗理论的贡献,三在新诗创作理论上的卓越贡献。四俞平伯的诗歌创作理论,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文学评论》原副主编王保生研究员在《俞平伯和他的散文创作》中认为:一九二二年三月,胡适在为《申报》五十年纪念刊所写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一文中,最先总结了五四以来现代散文创作方面的成就,“周作人的小品文,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是成了一个很有权威的流派。”而在周作人这一“很有权威”的散文流派中,俞平伯和废名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们构成了这一流派的两翼。他们用一种恬淡的心情来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世界,他们虽则也有爱憎,有悲欢,但一般都不用强烈的词句,而出之以平和的语调,比较舒缓的节奏,似乎是夏夜乘凉,摇扇清谈,清风徐来,欲念顿消,一切显得那么谐和,那么舒适。这种境界,既是他们文章的共同风格,也是他们共同追求的理想生活境界。
在文字技巧上,周作人、俞平伯等并不固执地专用一种语言,他们的目标是,一要有趣味,二要有知识,三要有雅致的气味,因此他们讲究“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揉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所以他们的散文作品,不象新文学运动初期的作品那样,欧化现象比较严重,他们的散文小品,更多地从现实生活和古代作品里吸取语言的营养,有着比较浓厚的民族气质。
综观俞平伯的小品散文,我们可以发见,他虽则经受过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甚至还到美国游历过,但是从思想深处来看,他仍是一个较多地保留着我国古代名士气质的知识分子。他不同于徐志摩、陈西滢那样洋味十足,文中散发着一种外国绅士气,甚至也不同于周作人的中外兼收,他的思想、性格和趣味,完全是中国式的,他的散文在思想上,就有着一种中国名士凤。与此相适应,他在艺术上追求的是一种雅致和趣味。这种名士思想和雅致、洒脱的文风,就构成了俞平伯散文的第三个特色。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委张中良研究员《俞平伯诗歌创作的新与旧》的发言谈到:俞平伯文言旧体诗创作早于白话新诗创作,现存者即有1916年所作旧体诗。他的第一部新诗集《冬夜》里所收作品,最早的为
尽管俞平伯在《冬夜·自序》中表白“不愿顾念一切做诗底律令”,但旧体诗词修养在其新诗创作中不可避免地打上鲜明的烙印。朱自清在《冬夜》初版《序》中称赞俞平伯新诗的特色之一为“精炼的词句和音律”,“他诗里有种特异的修辞法,就是偶句。偶句用得适当时,很足以帮助意境和音律底凝练。平伯诗里用偶句极多,也极好。”“平伯诗底音律似乎已到了繁与细底地步;所以凝练,幽深,绵密,有‘不可把捉的风韵’。”朱自清肯定的俞平伯新诗风格的多样化与情景相融的写法,也或多或少与传统文学的熏陶有关。
湖州师范学院余连祥教授《俞平伯与朴社》的发言中谈到:俞平伯不是朴社的发起人,但他不久就加入了,且非常热心朴社出版事宜。朴社最早推出的是俞平伯主持的“霜枫小丛书”。俞平伯对《浮生六记》的校点,非常成功。俞平伯充分发挥其从乾嘉学派那里传承来的校勘功夫,又加点了新式标点,还会在报刊上评点介绍此书,很快让《浮生六记》风靡文坛。在朴社出版的62种图书中,《浮生六记》一版再版,发行量仅次于顾颉刚编的《古史辨》第一辑。目前《浮生六记》已有一百多种版本,但最经典的还是俞平伯校点的本子。
俞平伯为北平朴社做的最为“示美”的图书是诗集《忆》。《忆》的封面是请孙福熙设计,灰底上的白点犹如一朵朵飘舞的雪花。插图是请丰子恺画的18幅彩色漫画。朱自清
《文学评论》编辑李超在《旧诗词与新散文:新旧交替时代,一个文人对自己情性的坚守》的发言中认为:俞平伯先生的一生几乎横跨了整个二十世纪,而他的青年时代正处在国家多难,知识分子为民族存亡振臂高呼的年代,他是这个时代的见证人,更是一个亲历者,在那个崇尚新、批判旧到有些偏执的时代里,俞平伯只是认真地做了他自己。
读俞平伯的白话诗和散文,无不感受到他对自己追求的一以贯之。我们从他的字里行间感受到那种幽深婉曲的情致,那里含有江南才子的细腻多情,并最终直插入人生根本问题的纠结中,这里又包含着他对人生的深沉的爱恋。同时的人们常批评他的散文文词枝蔓,语意晦涩,批评他的诗过于喜欢谈哲理,我以为这正是俞平伯的精神特质,是他内心的节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文心之细,细若牛毛;文事之危,危如累卵”,而“灵魂的冒险”便是“做诗”。的确,他的散文很容易陷入一种暮气,但简单地他这种气质归结为旧式文人的情感,则是那个时代的烙印,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不妨看作他性格使然,其实中国文人从古至今都有伤春悲秋的特质,即使在今天依然派遣不掉这样的伤逝情怀,又何限于俞平伯先生一人呢?
湖州师范学院王昌忠博士在《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论俞平伯的诗学选择》中认为:俞平伯是中国早期的一位写作新诗的诗人,出版有《冬夜》、《西还》、《忆》等新诗集;同时也是中国现代较早的诗论家。从“五四”到二十年代中期,他发表了十多篇诗论文章。其中如《白话诗的三大条件》、《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作诗的一点经验》、《诗底自由和普遍》、《〈冬夜〉自序》、《诗底进化的还原论》等,均颇有见地,自成一家,对早期的新诗创作和新诗理论建设,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透过其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文章,可以看出其诗学观念是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
受传统与现代前后两只手的拽拉,俞平伯的诗学立场有矛盾、犹豫之处,也有调和、融合之处,从而显示出了那个时代固有的色彩。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俞平伯的诗学观念因此而显得中庸、平和,减弱了其革命性、锋利性。
三、德清俞氏家族与江南文化世家:
德清俞氏家族,为中国近现代显赫的文化世家,在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史、文学史、学术史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曾祖俞樾,进士及第,著有《春在堂全集》,晚清朴学大师。部分与会专家发表了有关俞樾的研究观点。
社科院文学所王达敏研究员在《俞樾与桐城派》的发言中谈到:在晚清,曾国藩作为政坛、学界重镇,推扬桐城派不遗余力。俞樾作为曾氏门生,对桐城派褒贬兼有。他认为,古文至明代衰甚,或媚于世俗,或佶屈聱牙。桐城方苞、姚鼐出,起衰救弊,为文谨严有法,始追及于古之作者。桐城嫡派之文,原本经史,抒写性真,粹然儒者之言,而结体谨严,选词雅洁,无叫嚣之气,无涤滥之音。但是,他也认为,以桐城之法绳天下之文,则非通论。桐城末流之文,貌为高古,实则空疏;貌为淸真,实则枯涩。他对论者以桐城之文为文家正宗深不以为然,以为骈俪之文才是文之正轨。俞樾作为汉学宗师,对桐城派之贬,与乾嘉诸老一脉相承,且影响深远。俞门弟子章太炎对桐城派评价不高,章门弟子钱玄同等视桐城派为谬种,追本溯源,皆与俞樾贬抑桐城派的见解有关。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陈才智博士《俞曲园与白香山的诗歌渊源》的发言中认为:白香山人称“广大教化主”,对后代文人的影响深远而广泛。降及晚清诗坛,香山流风仍在,俞曲园堪为代表。曲园一生与诗结缘;七十二年间,诗歌是曲园唯一没有停辍的文体。这种不辍吟咏,嗜诗如命,近乎痴迷的诗歌创作态度,以及“随笔而书”“不雕不琢”的创作取向,都令人不免联想到千载以前的白香山。俞樾的诗集,完全可视为俞樾的诗体自传或日记,乃至自修年谱。这一点也堪与白香山媲美。
俞樾虽为硕学鸿儒,“精研朴学”但诗歌语言却务求浅切,往往直接状物抒情,喜用并擅用白描。还常以俗语入诗。具体而言,俞曲园诗歌瓣香白香山,取法乐天体,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分析。第一,体现在创作内容和题材上感时而发,遵循兴谕规刺的创作意旨,忧时感事的乐府传统。第二,体现在诗歌语言的浅切直白,艺术风格的通俗浅切、畅达流利。俞樾的诗歌,触境而发,称意而言,朴实而又清新,通俗而又形象,没有晦涩的语言,也没有艰深的意境,而是娓娓道来,通俗易懂,不愧是晚清诗坛承继香山体衣钵的代表诗人。
此外,湖州师范学院胡淑娟教授在《俞平伯古典词论的当下价值》发言中谈到:俞平伯以风范,即读书是乐趣,而非任务,是一位不为“奖学金”读书的人。“为人老成持重,淡泊自甘,是以为纯正的学者”,趣味广,诗书画等无所不工,现当代士林的典范。严谨求实的阅读态度,使其独步诗词批评的舞台,有着自己独到的心灵感悟。
对于这次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会所取得的成果,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陆建德研究员在会议总结中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同时对于俞平伯研究的学术发展,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思路。
(本版照片均由文学研究所高力生先生摄)
|
|
|
左起:程民、杨槐、陆建德、朱渊寿、邓绍基、张林华、蒋云良、俞昌时 |
|
|
|
左起:陆建德、朱渊寿、邓绍基 |
|
|
|
左起:陆永品、刘扬忠、胡明、邓绍基、王保生 |
|
|
|
左起:邓绍基、张林华、蒋云良、俞昌实 |
|
|
|
王保生、陆永品 |
|
|
|
刘扬忠、胡明与俞昌实夫妇 |
|
|
|
刘扬忠、胡明 |
|
|
|
孙丽华、刘方、张国星 |
|
|
|
余连祥、孙玉明 |
|
|
|
王达敏、李超 |
|
|
|
夏薇、孙丽华 |
|
|
|
周云水、陈如尧 |
|
|
|
左起:胡淑娟、刘方、杜隽、余连祥 |
|
|
|
会场 |
您是第 12651820 位访问者 备京ICP备:06036494号-20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 《外国文学评论》编辑部
电话:010-85195583(周二、周三) 邮编:100732
本系统由北京博渊星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设计开发 技术支持电话:010-63269626